伊斯兰妇女观与其它妇女观之比较
 伊斯兰妇女观与其它妇女观之比较
伊斯兰妇女观与其它妇女观之比较
自人类有史以来,对于妇女问题,各种文化实体和各种学派持有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
佛教认为,女人具有“五漏之体”,而男人则“身具七宝”。(《佛说大乘金刚经论》),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透得此门,出尘罗汉。(《佛说四十二章经解》)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第十七)朱熹注说:”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后来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天尊地卑,男贵女贱”的观点,认为: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春秋繁露·基义》)针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和父权思想,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提出异议。如明代后期的李贽曾批判儒家两性不平等的社会伦理观,认为:“夫妇,人之始也……夫妇正,然后万事万物无不出于正矣。”(《初潭集.夫妇篇总论》)明王文录一针见血地指出:“古礼父重而母轻……制礼者乃男子,故父重,为己谋,私且偏也。”(《海沂子.敦原篇》)
犹太——基督教神学在男女起源问题上和孔子“阳卦奇,阴卦耦”(《系辞下》)“一能生二”的阴阳之变说颇有些相似,即认为夏娃(女人)是从亚当(男人)的肋骨创造出来的。
这似乎是用寓体的符号来书写同一个哲学命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夏娃是亚当的附属品。事实上夏娃被创造时就是亚当的平等配偶,她永远应当是他的平等配偶。然而,犹太——基督教神学却将“原罪”仅归咎于夏娃一个人。“就这样,运用创世教义奠定了两性的不平等和妇女的奴役地位。”(皮埃尔·勒鲁《论平等》,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1页)。
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密尔顿对希伯来人神话中的起源优先说更是深信不疑。他把妇女看作是一种自身无法到达上帝那里的下等人,认为夏娃只有通过亚当才能认识上帝——“他只向着上帝,她通过他向着上帝。”亚里土多德也是如此,他在论述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时说:“两性关系也类似于此:一个进行指挥,另一个服从。”(《政治学》卷一第二章)具体地说,“家庭的管理建立在三种权力基础上:统治权、父权和夫权……妇女虽有某种意志,却处于隶属地位。”(同上第五章)柏拉图在妇女问题上的观念并不比亚里土多德宽容些。他不懂得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平等地位。这就是说为何当妇女被男人同化时。“他把妇女作为一种低等生物,无需根据什么法律条文就交给男人。”(皮埃·勒鲁《论平等》第116页)
在古代印度,妇女整日依附于男人的“保护”,没有人身权、继承权。而在英国,根据当时的共同法,丈夫不仅可以占有而且可以随意处置妻子的财产。“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尤其贬低女性……妇女被看作是地狱之门和人类各种罪恶的渊薮妇女应为自己而感到羞耻。她们必须因自己给世界带来的诅咒和灾难而永远不停地赎罪。”(戴维《东西方的婚姻》)
在古希腊和罗马,妇女确实被看成是另外一类不同的人,一种和男人有着本质上差别的人。希腊古典时期的文学、宗教、艺术都反映这种观念:妇女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她们也代表了自然界一切原始的、反社会的因素;而文明世界是男人征服自然界、控制一切原始的欲望,在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征服必然也包括对妇女的征服,即以一种厌恶女人,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的态度克制对她们的欲望。因此,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妇女是文明的敌人。古希腊和罗马的建筑师常用女像往来支撑象征父权统治的高大建筑。古希腊罗马法不承认妇女有任何自主权,将她们永远置于男性的督管之下。罗马教会甚至判定“妇女无灵魂”,死后不可复生。
即便在自称最发达的现代西方,性别歧视仍然存在。这或多或少可以看成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一基督教文化在现代西方人心灵上的历史沉淀。《性:妇女受压迫的基础》一书的作者凯瑟琳·麦金农曾制定“明尼阿波利斯法规”,该法规认定充斥西方世界的黄色书画是把妇女等同于商品,是性别歧视的表现,并主张给予受黄色书画侵害的所有妇女以一种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麦金农认为,男性往往通过在黄色书画中表现妇女以及通过强奸的威胁来达到控制和羞辱的目的。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典型的男性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所推崇和表现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不仅基本上是由掌握政治权力的男性所确定的,而且与体现男性而不是女性本质与成就的西方人文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克斯蒂娜·斯特德在其代表作《爱孩子的人》中就曾借女主人公亨妮之口向“所有手里握着王牌的男人”提出抗议。亨妮的女儿路易则是一位泼辣的行动主义者。她们以家庭为舞台上演的一部又一部闹剧反映了西方家庭面临瓦解,道德面临沦丧的可悲情景。
《女性的学问》一书的作者格伦敦对西方各种有关坠胎和离婚的法律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建立在强有力的隐私权之上的坠胎与双方均不承担责任的离婚,在强调婚姻是个人的自我实现的同时,公开表达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并忽视了与之同在的社会伦理观,后者承认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与抚养儿童的价值,并且肯定胎儿生命的价值。(参见尼科拉·雷西《女权主义者的法律理论》,载《法学译丛))1992年第3期)格伦敦主张建立一种旨在保障妇女权益的家庭政策(包括尊重胎儿的生命,抚育和赡养他人等)。她认为,美国等国家缺少这种家庭政策暴露了它自由个人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鼓励自私自利并拒绝探求能够平衡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政治妥协。
然而,女权主义者在猛烈抨击男性社会弊端的同时,往往走向另一极端,即将自己和男性对立起来,试图把女性亚文化改造成一种主导文化并用它去替代男性文化。由于过度地宣扬自由和解放,最后造成婚姻危机、独身主义和同性恋等社会负面效应。这样的妇女已蜕变为不知羞耻的维纳斯,既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也丧失了作为女人的尊严。
事实上,远至孔子、亚里土多德和柏拉图,近至现代女权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都无法找到一种完善的答案。不是宣扬男尊女卑,就是宣扬女权至上(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中的激进派)。前者意在完全剥夺妇女应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买卖治产权以及参与社会工作和管理的权利等等,将她们禁锢在家庭的狭小天地里;后者在否定男性文化的同时,往往不顾妇女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将她们和男人等量齐观,以致她们逐渐淡化自己在家庭中所承担的母性责任,异化为男性的“公平竞争者”。
唯有伊斯兰的妇女观能够兼顾妇女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将她们安置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她们既不是男人的奴隶,也不是男人的竞争对手。伊斯兰的这种协调功能能够把社会维系于一种均衡的状态。它本身所蕴含的智慧便是真理的展现。
首先,伊斯兰主张妇女在人格上与男人平等。伊斯兰不把“原罪”仅仅责咎于哈娃(夏娃)一人,《古兰》上说:阿丹(亚当)和哈娃(夏娃)两个人都受到了引诱,他们两都犯了罪,并说当他俩表示忏悔之后,安拉对两个人都予以宽恕。而且,安拉总是将他俩合在一起称呼的。(参见古兰2:35、7:19-27、20:117-123)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由“原罪”说中产生的男人对女人的偏见。
其次,伊斯兰倡导妇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男子平等。在经济上,伊斯兰允许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签订契约、经营企业、赚取金钱和治理财产等权利。在政治上,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也有参予政治和管理国家的权利。正如《古兰》所说:(“妇女有同等的权利。”)(2:228)然而,权利总是和义务(即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多一点权利,也就意味着多一点义务。因此,考虑到丈夫赡养妻室儿女的责任之重大,《古兰》规定,在遗产的分配与获得方面,男子高出女子一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否则,一意刻求表面上的、数量上的均等最终反而会破坏平等本身。
第三,伊斯兰在强调妇女在求知及受教育方面跟男子是平等的。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穆罕默德先知就郑重宣布:求知是每一位男女穆斯林的天职。在当时麦地那清真寺,妇女和男子一样聆听先知的演讲,并且有权提出各种问题请先知解答。在她们中间曾造就了一批德材兼备的女学者。有精通《古兰》的经学家,通晓教律的法学家和研究语言文学的专家等。阿依莎就是其中最为典型、最为著名的一个。甚至许多男子都向她请教有关《古兰》和教律方面的知识。
第四,伊斯兰给予妇女婚姻上的自主权。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过:“不和寡妇商量,就不能和她结婚,不经少女同意,不能和她结婚。她的同意就是沉默。”(《布哈里圣训集》)甚至在婚礼举行后,如果她宣布她不同意,婚姻即刻解除。大家还知道,伊斯兰允许一夫多妻,但多妻以四位为限,且丈夫必须公平待妻,否则只可有一妻。多妻的男子如果不能公平待妻,则妻可向法庭起诉,要求脱离夫妻关系。再者,男子欲娶第二妻,须得第一妻的同意。否则,其妻可向法庭提出控告。而且初婚的女子可向男子提出不二婚的条件。(参见海维谅泽《伊斯兰人权论丛》,台北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1978年版第145-154页)。
第五,伊斯兰极其尊重和爱护母亲,将善待母亲和妻子视为每个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责任。先知穆罕默德曾说:“你们善待母亲,你们的天堂是在母亲的脚下。”一次,一个人询问先知“谁最应受我的照顾?”他说:“你母亲。”那人说:“然后是谁?”先知说:“然后是你的母亲。”那人又问道:“然后呢?”先知还是说:“你母亲!”那人再一次问道:“然后呢?”先 知说:“然后是你的父亲!”(《布哈里、穆斯林圣认;集》)先知还说:“你们当中对妻子最和善的人,就是你们中最好的人。从我对妻子的态度看,我是你们中最好的人。”(转引自穆·库特卜《伊斯兰:被误解了的宗教》中“伊斯兰和妇女”一文)
第六,伊斯兰倡导家庭民主,主张夫妻相互协商,相互合作。丈夫要“以仁慈的方式去和她们商量”。不能一意孤行,武断专横。丈夫赡养妻室儿女只意味着多一份义务和责任,不能因此而成为家庭的专制君王。况且,夫妻相互了解和谅解是家庭生活的感情基础。
第七,伊斯兰认为,妇女和男子是一种互为依托,相互补充的关系。“她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她们的衣服。”(2:187)。既不把女子和男子对立起来,也不把女子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对立起来。做一个贤妻良母,抚育子女成长是妇女的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这是由妇女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现代社会心理学证明了妇女这一家庭责任的重要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妇女不要接受教育。若不接受教育,她们怎么能担当起抚育孩子的重任呢?这也绝不意味着妇女不能成为社会的劳动成员或无权参与社会的管理工作。历史上,哈里发艾卜·伯克尔(632—634年任职)的妻子阿斯玛(Asma)就曾离家做工,以减轻丈夫的负担。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本·赫塔布(634-644年任职)执政期间,麦地那贸易市场就有许多女商人。欧麦尔曾推选一位名叫希发(Shifa)的妇女管理麦地那市场。但是,妇女的社会责任只是第二位的,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以社会责任去取代家庭责任。
总之,从伊斯兰妇女观与其他妇女观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伊斯兰妇女观是站在宇宙的高度来审度妇女问题的。它是安拉的迹象,也是安拉的定制。它以一种清澈见底的整体视觉取代了人类由于自身的脆弱而形成的各种偏见。伊斯兰给予妇女的权利和优惠是其它任何宗教制度和世俗制度所无法比拟的。
佛教认为,女人具有“五漏之体”,而男人则“身具七宝”。(《佛说大乘金刚经论》),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透得此门,出尘罗汉。(《佛说四十二章经解》)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第十七)朱熹注说:”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后来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天尊地卑,男贵女贱”的观点,认为: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春秋繁露·基义》)针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和父权思想,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提出异议。如明代后期的李贽曾批判儒家两性不平等的社会伦理观,认为:“夫妇,人之始也……夫妇正,然后万事万物无不出于正矣。”(《初潭集.夫妇篇总论》)明王文录一针见血地指出:“古礼父重而母轻……制礼者乃男子,故父重,为己谋,私且偏也。”(《海沂子.敦原篇》)
犹太——基督教神学在男女起源问题上和孔子“阳卦奇,阴卦耦”(《系辞下》)“一能生二”的阴阳之变说颇有些相似,即认为夏娃(女人)是从亚当(男人)的肋骨创造出来的。
这似乎是用寓体的符号来书写同一个哲学命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夏娃是亚当的附属品。事实上夏娃被创造时就是亚当的平等配偶,她永远应当是他的平等配偶。然而,犹太——基督教神学却将“原罪”仅归咎于夏娃一个人。“就这样,运用创世教义奠定了两性的不平等和妇女的奴役地位。”(皮埃尔·勒鲁《论平等》,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1页)。
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密尔顿对希伯来人神话中的起源优先说更是深信不疑。他把妇女看作是一种自身无法到达上帝那里的下等人,认为夏娃只有通过亚当才能认识上帝——“他只向着上帝,她通过他向着上帝。”亚里土多德也是如此,他在论述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时说:“两性关系也类似于此:一个进行指挥,另一个服从。”(《政治学》卷一第二章)具体地说,“家庭的管理建立在三种权力基础上:统治权、父权和夫权……妇女虽有某种意志,却处于隶属地位。”(同上第五章)柏拉图在妇女问题上的观念并不比亚里土多德宽容些。他不懂得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平等地位。这就是说为何当妇女被男人同化时。“他把妇女作为一种低等生物,无需根据什么法律条文就交给男人。”(皮埃·勒鲁《论平等》第116页)
在古代印度,妇女整日依附于男人的“保护”,没有人身权、继承权。而在英国,根据当时的共同法,丈夫不仅可以占有而且可以随意处置妻子的财产。“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尤其贬低女性……妇女被看作是地狱之门和人类各种罪恶的渊薮妇女应为自己而感到羞耻。她们必须因自己给世界带来的诅咒和灾难而永远不停地赎罪。”(戴维《东西方的婚姻》)
在古希腊和罗马,妇女确实被看成是另外一类不同的人,一种和男人有着本质上差别的人。希腊古典时期的文学、宗教、艺术都反映这种观念:妇女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她们也代表了自然界一切原始的、反社会的因素;而文明世界是男人征服自然界、控制一切原始的欲望,在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征服必然也包括对妇女的征服,即以一种厌恶女人,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的态度克制对她们的欲望。因此,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妇女是文明的敌人。古希腊和罗马的建筑师常用女像往来支撑象征父权统治的高大建筑。古希腊罗马法不承认妇女有任何自主权,将她们永远置于男性的督管之下。罗马教会甚至判定“妇女无灵魂”,死后不可复生。
即便在自称最发达的现代西方,性别歧视仍然存在。这或多或少可以看成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一基督教文化在现代西方人心灵上的历史沉淀。《性:妇女受压迫的基础》一书的作者凯瑟琳·麦金农曾制定“明尼阿波利斯法规”,该法规认定充斥西方世界的黄色书画是把妇女等同于商品,是性别歧视的表现,并主张给予受黄色书画侵害的所有妇女以一种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麦金农认为,男性往往通过在黄色书画中表现妇女以及通过强奸的威胁来达到控制和羞辱的目的。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典型的男性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所推崇和表现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不仅基本上是由掌握政治权力的男性所确定的,而且与体现男性而不是女性本质与成就的西方人文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克斯蒂娜·斯特德在其代表作《爱孩子的人》中就曾借女主人公亨妮之口向“所有手里握着王牌的男人”提出抗议。亨妮的女儿路易则是一位泼辣的行动主义者。她们以家庭为舞台上演的一部又一部闹剧反映了西方家庭面临瓦解,道德面临沦丧的可悲情景。
《女性的学问》一书的作者格伦敦对西方各种有关坠胎和离婚的法律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建立在强有力的隐私权之上的坠胎与双方均不承担责任的离婚,在强调婚姻是个人的自我实现的同时,公开表达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并忽视了与之同在的社会伦理观,后者承认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与抚养儿童的价值,并且肯定胎儿生命的价值。(参见尼科拉·雷西《女权主义者的法律理论》,载《法学译丛))1992年第3期)格伦敦主张建立一种旨在保障妇女权益的家庭政策(包括尊重胎儿的生命,抚育和赡养他人等)。她认为,美国等国家缺少这种家庭政策暴露了它自由个人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鼓励自私自利并拒绝探求能够平衡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政治妥协。
然而,女权主义者在猛烈抨击男性社会弊端的同时,往往走向另一极端,即将自己和男性对立起来,试图把女性亚文化改造成一种主导文化并用它去替代男性文化。由于过度地宣扬自由和解放,最后造成婚姻危机、独身主义和同性恋等社会负面效应。这样的妇女已蜕变为不知羞耻的维纳斯,既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也丧失了作为女人的尊严。
事实上,远至孔子、亚里土多德和柏拉图,近至现代女权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都无法找到一种完善的答案。不是宣扬男尊女卑,就是宣扬女权至上(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中的激进派)。前者意在完全剥夺妇女应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买卖治产权以及参与社会工作和管理的权利等等,将她们禁锢在家庭的狭小天地里;后者在否定男性文化的同时,往往不顾妇女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将她们和男人等量齐观,以致她们逐渐淡化自己在家庭中所承担的母性责任,异化为男性的“公平竞争者”。
唯有伊斯兰的妇女观能够兼顾妇女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将她们安置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她们既不是男人的奴隶,也不是男人的竞争对手。伊斯兰的这种协调功能能够把社会维系于一种均衡的状态。它本身所蕴含的智慧便是真理的展现。
首先,伊斯兰主张妇女在人格上与男人平等。伊斯兰不把“原罪”仅仅责咎于哈娃(夏娃)一人,《古兰》上说:阿丹(亚当)和哈娃(夏娃)两个人都受到了引诱,他们两都犯了罪,并说当他俩表示忏悔之后,安拉对两个人都予以宽恕。而且,安拉总是将他俩合在一起称呼的。(参见古兰2:35、7:19-27、20:117-123)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由“原罪”说中产生的男人对女人的偏见。
其次,伊斯兰倡导妇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男子平等。在经济上,伊斯兰允许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签订契约、经营企业、赚取金钱和治理财产等权利。在政治上,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也有参予政治和管理国家的权利。正如《古兰》所说:(“妇女有同等的权利。”)(2:228)然而,权利总是和义务(即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多一点权利,也就意味着多一点义务。因此,考虑到丈夫赡养妻室儿女的责任之重大,《古兰》规定,在遗产的分配与获得方面,男子高出女子一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否则,一意刻求表面上的、数量上的均等最终反而会破坏平等本身。
第三,伊斯兰在强调妇女在求知及受教育方面跟男子是平等的。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穆罕默德先知就郑重宣布:求知是每一位男女穆斯林的天职。在当时麦地那清真寺,妇女和男子一样聆听先知的演讲,并且有权提出各种问题请先知解答。在她们中间曾造就了一批德材兼备的女学者。有精通《古兰》的经学家,通晓教律的法学家和研究语言文学的专家等。阿依莎就是其中最为典型、最为著名的一个。甚至许多男子都向她请教有关《古兰》和教律方面的知识。
第四,伊斯兰给予妇女婚姻上的自主权。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过:“不和寡妇商量,就不能和她结婚,不经少女同意,不能和她结婚。她的同意就是沉默。”(《布哈里圣训集》)甚至在婚礼举行后,如果她宣布她不同意,婚姻即刻解除。大家还知道,伊斯兰允许一夫多妻,但多妻以四位为限,且丈夫必须公平待妻,否则只可有一妻。多妻的男子如果不能公平待妻,则妻可向法庭起诉,要求脱离夫妻关系。再者,男子欲娶第二妻,须得第一妻的同意。否则,其妻可向法庭提出控告。而且初婚的女子可向男子提出不二婚的条件。(参见海维谅泽《伊斯兰人权论丛》,台北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1978年版第145-154页)。
第五,伊斯兰极其尊重和爱护母亲,将善待母亲和妻子视为每个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责任。先知穆罕默德曾说:“你们善待母亲,你们的天堂是在母亲的脚下。”一次,一个人询问先知“谁最应受我的照顾?”他说:“你母亲。”那人说:“然后是谁?”先知说:“然后是你的母亲。”那人又问道:“然后呢?”先知还是说:“你母亲!”那人再一次问道:“然后呢?”先 知说:“然后是你的父亲!”(《布哈里、穆斯林圣认;集》)先知还说:“你们当中对妻子最和善的人,就是你们中最好的人。从我对妻子的态度看,我是你们中最好的人。”(转引自穆·库特卜《伊斯兰:被误解了的宗教》中“伊斯兰和妇女”一文)
第六,伊斯兰倡导家庭民主,主张夫妻相互协商,相互合作。丈夫要“以仁慈的方式去和她们商量”。不能一意孤行,武断专横。丈夫赡养妻室儿女只意味着多一份义务和责任,不能因此而成为家庭的专制君王。况且,夫妻相互了解和谅解是家庭生活的感情基础。
第七,伊斯兰认为,妇女和男子是一种互为依托,相互补充的关系。“她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她们的衣服。”(2:187)。既不把女子和男子对立起来,也不把女子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对立起来。做一个贤妻良母,抚育子女成长是妇女的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这是由妇女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现代社会心理学证明了妇女这一家庭责任的重要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妇女不要接受教育。若不接受教育,她们怎么能担当起抚育孩子的重任呢?这也绝不意味着妇女不能成为社会的劳动成员或无权参与社会的管理工作。历史上,哈里发艾卜·伯克尔(632—634年任职)的妻子阿斯玛(Asma)就曾离家做工,以减轻丈夫的负担。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本·赫塔布(634-644年任职)执政期间,麦地那贸易市场就有许多女商人。欧麦尔曾推选一位名叫希发(Shifa)的妇女管理麦地那市场。但是,妇女的社会责任只是第二位的,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以社会责任去取代家庭责任。
总之,从伊斯兰妇女观与其他妇女观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伊斯兰妇女观是站在宇宙的高度来审度妇女问题的。它是安拉的迹象,也是安拉的定制。它以一种清澈见底的整体视觉取代了人类由于自身的脆弱而形成的各种偏见。伊斯兰给予妇女的权利和优惠是其它任何宗教制度和世俗制度所无法比拟的。
saierde- 正式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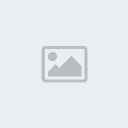
- 帖子数 : 19
注册日期 : 08-03-15
您在这个论坛的权限: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回复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