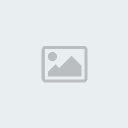中国离诚信社会还有多远?
 中国离诚信社会还有多远?
中国离诚信社会还有多远?
中国离诚信社会还有多远?——读科尔奈《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有感
在午夜空无一人的街头,你还会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规吗?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站,提着大包小包的你,会坦然接受一个陌生人的热情相助吗?
我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答案都是“不会”。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答案都和我一样。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背后,我们发现了“诚实与信任”的幽灵。是的,这个幽灵在我们中间游荡,挥之不去。于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地铁口,“发票、发票”的叫声不绝于耳;街道旁,抱孩子的大嫂热情地向你兜售光盘;天桥上,“办证”的小广告一串又一串;还有那假烟、假药、假文凭、统计水分、学术***、金融诈骗、股市造假、基金黑幕……
诚实与信任缺失的问题肯定不是中国独有。所以雅诺什•科尔奈教授所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才以此为题,聚集世界上17个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展了专门的深入研究。科尔奈教授的文章《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见《比较》第9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就是基于此项研究的个人感受。
在中国经济学界,科尔奈教授的盛名几乎无人不晓,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典著作《短缺经济学》。在研究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大概迄今无人能出其右。而今,沧桑巨变之后,科尔奈教授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了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而且聚焦在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诚实与信任”问题上。
科尔奈教授谈到了两类诚实与信任关系:市场交易的主体即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国家不能有效保障商业合同的履行,黑手党和犯罪行为的滋生就无法避免。而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以法律为权威的制度体系的构建,需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但这方面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构建诚信社会更为关键和根本的战略是公民“心态”的改变。科尔奈举了这么一个生动的例子:
“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正在收听一个热线广播。当时主持人要求听众举例说他们在国外度假回来时如何逃避关税。他们得说出最刺激的冒险经历。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人们吹嘘着他们是如何成功违规并欺骗国家的。当然,我清楚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即使在最守法的国家也会经常发生。主要的区别不在于逃避关税的频率,而在于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美国或挪威的电台主持人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听众也不会就此吹嘘。逃税无处不在,但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此感到羞耻,不会在社交场合对此津津乐道。”
科尔奈认识到,在大一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国家无数的管制和命令来调节的。因此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诚信履约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就成为一个很基本的要求。既然重塑人们的心态不可能那么快实现,我们就必须寄希望于长期的努力。科尔奈提到的办法包括:家庭、中小学和大学的教化与教育,平面媒体和电视潜移默化的作用,公众人物与工作上司言行的影响。
科尔奈最后的忠告是:“重任未有穷期。我期望自己,以及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位成员,都保持必要的耐心和容忍。”
读罢科翁的大作,掩卷之余,不由得对我们中国的现实多了一层“历史深处的忧虑”。不错,中国和东欧国家一样,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但中国更独特的情况是,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一直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市场从来没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唱过主角。
小农生活在人数不多的村落中,以土地为生,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亲戚邻里,极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因而这种经济模式下沉淀的文化就是:重人情而轻规则(遇事不依制度而诉诸“关系”、“后门”),重空间而轻时间 (老乡观念强,守时观念差)。这样的文化资源,用以应付村落里熟人间的关系自然没问题,但如果要和陌生人做生意,就有些不够用了。
如何和陌生人(这里指的是非亲戚、非老乡的外地人)打交道?中国传统文化教给我们的是两个字:一曰“忠”,二曰“义”。
“忠”用以协调自己(奴才)与作为陌生人的上司(主子)的关系,所谓“一仆不事二主”。而“义”则是用以协调自己和作为陌生人的朋友的关系,所谓“哥们义气”,“结义兄弟”。而集“忠”、“义”于一身者,最典型的则非关羽莫属。关羽与刘备,既是仆主关系,又是结拜弟兄关系,因此“忠”、“义”都需要。
有意思的是,关羽作为一名战将,武功决非后世小说描绘的那么高强,加之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终于酿成杀身大祸;而且“大意失荆州”,颠覆蜀汉有利战略格局,过失不小。当时的人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就曾封关羽为“归缪侯”,语气间多有不屑。(顺便说一句,刘禅或许并非如后世所说的那么弱智,或许他对于诸葛亮北伐劳而无功的结果早已心知肚明,所谓“英雄拗不过时势”,而且他的“此间乐,不思蜀”也体现了极高的生存智慧,远非南唐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可比。)
可是历史越往后翻,关羽身价越高。宋代以降,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关羽多次为朝廷所封,地位越来越高,成了与孔夫子比肩的“武圣人”。关羽身价一路走高,折射的是市场因素开始在这个小农国度逐步“发酵”的事实。道理很清楚,商业越来越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与陌生人做生意,如何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呢?关羽“千里走单骑”“义薄云天”的传奇就在铜钱的计算声中粉墨登场了。
商业生意倚重“义”文化,是在我们这个小农国家发展出来的必然逻辑。所以直至今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酒桌上的生意”,所谓“生意不成仁义在”。陌生人之间的生意关系,一定要发展到朋友之间的“义气”的程度,才算可靠。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逻辑。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总是请人去吃“花酒”,看来真的是选对了地方。
可惜的是,“义气”要求双方的交情发展到一定的深度,这不是所有的买卖关系所能具备的。在“义气”的故纸堆里,我们看到的只是放大的“人情”,找不到“法治规则”的身影。更何况,小农的思想里,本身就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欺生”的狡黠。因为他与外界的交易,即使有,也往往是一次性的,故而“欺骗一次又何妨”。
于是我们见到了今天中国市场秩序中诚信的极度缺失。这个问题恐怕不是靠弘扬传统的“义”文化所能解决的。我想问的是,平等、诚信、负责的商业精神的种子,在中国这块缺少适宜养分的土地上,能否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抑或,就象西方文明的其他因子在中国的命运一样,等待我们的又是一场“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的结局?
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一些有良心的学者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我理解,诚信文化在全社会普遍的养成,本身就是“好的市场经济”所依赖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诚信立法”,这个过程一定会比较缓慢,所以,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容忍”。作者:赵少钦
在午夜空无一人的街头,你还会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规吗?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站,提着大包小包的你,会坦然接受一个陌生人的热情相助吗?
我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答案都是“不会”。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答案都和我一样。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背后,我们发现了“诚实与信任”的幽灵。是的,这个幽灵在我们中间游荡,挥之不去。于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地铁口,“发票、发票”的叫声不绝于耳;街道旁,抱孩子的大嫂热情地向你兜售光盘;天桥上,“办证”的小广告一串又一串;还有那假烟、假药、假文凭、统计水分、学术***、金融诈骗、股市造假、基金黑幕……
诚实与信任缺失的问题肯定不是中国独有。所以雅诺什•科尔奈教授所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才以此为题,聚集世界上17个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展了专门的深入研究。科尔奈教授的文章《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见《比较》第9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就是基于此项研究的个人感受。
在中国经济学界,科尔奈教授的盛名几乎无人不晓,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典著作《短缺经济学》。在研究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大概迄今无人能出其右。而今,沧桑巨变之后,科尔奈教授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了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而且聚焦在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诚实与信任”问题上。
科尔奈教授谈到了两类诚实与信任关系:市场交易的主体即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国家不能有效保障商业合同的履行,黑手党和犯罪行为的滋生就无法避免。而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以法律为权威的制度体系的构建,需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但这方面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构建诚信社会更为关键和根本的战略是公民“心态”的改变。科尔奈举了这么一个生动的例子:
“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正在收听一个热线广播。当时主持人要求听众举例说他们在国外度假回来时如何逃避关税。他们得说出最刺激的冒险经历。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人们吹嘘着他们是如何成功违规并欺骗国家的。当然,我清楚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即使在最守法的国家也会经常发生。主要的区别不在于逃避关税的频率,而在于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美国或挪威的电台主持人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听众也不会就此吹嘘。逃税无处不在,但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此感到羞耻,不会在社交场合对此津津乐道。”
科尔奈认识到,在大一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国家无数的管制和命令来调节的。因此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诚信履约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就成为一个很基本的要求。既然重塑人们的心态不可能那么快实现,我们就必须寄希望于长期的努力。科尔奈提到的办法包括:家庭、中小学和大学的教化与教育,平面媒体和电视潜移默化的作用,公众人物与工作上司言行的影响。
科尔奈最后的忠告是:“重任未有穷期。我期望自己,以及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位成员,都保持必要的耐心和容忍。”
读罢科翁的大作,掩卷之余,不由得对我们中国的现实多了一层“历史深处的忧虑”。不错,中国和东欧国家一样,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但中国更独特的情况是,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一直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市场从来没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唱过主角。
小农生活在人数不多的村落中,以土地为生,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亲戚邻里,极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因而这种经济模式下沉淀的文化就是:重人情而轻规则(遇事不依制度而诉诸“关系”、“后门”),重空间而轻时间 (老乡观念强,守时观念差)。这样的文化资源,用以应付村落里熟人间的关系自然没问题,但如果要和陌生人做生意,就有些不够用了。
如何和陌生人(这里指的是非亲戚、非老乡的外地人)打交道?中国传统文化教给我们的是两个字:一曰“忠”,二曰“义”。
“忠”用以协调自己(奴才)与作为陌生人的上司(主子)的关系,所谓“一仆不事二主”。而“义”则是用以协调自己和作为陌生人的朋友的关系,所谓“哥们义气”,“结义兄弟”。而集“忠”、“义”于一身者,最典型的则非关羽莫属。关羽与刘备,既是仆主关系,又是结拜弟兄关系,因此“忠”、“义”都需要。
有意思的是,关羽作为一名战将,武功决非后世小说描绘的那么高强,加之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终于酿成杀身大祸;而且“大意失荆州”,颠覆蜀汉有利战略格局,过失不小。当时的人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就曾封关羽为“归缪侯”,语气间多有不屑。(顺便说一句,刘禅或许并非如后世所说的那么弱智,或许他对于诸葛亮北伐劳而无功的结果早已心知肚明,所谓“英雄拗不过时势”,而且他的“此间乐,不思蜀”也体现了极高的生存智慧,远非南唐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可比。)
可是历史越往后翻,关羽身价越高。宋代以降,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关羽多次为朝廷所封,地位越来越高,成了与孔夫子比肩的“武圣人”。关羽身价一路走高,折射的是市场因素开始在这个小农国度逐步“发酵”的事实。道理很清楚,商业越来越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与陌生人做生意,如何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呢?关羽“千里走单骑”“义薄云天”的传奇就在铜钱的计算声中粉墨登场了。
商业生意倚重“义”文化,是在我们这个小农国家发展出来的必然逻辑。所以直至今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酒桌上的生意”,所谓“生意不成仁义在”。陌生人之间的生意关系,一定要发展到朋友之间的“义气”的程度,才算可靠。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逻辑。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总是请人去吃“花酒”,看来真的是选对了地方。
可惜的是,“义气”要求双方的交情发展到一定的深度,这不是所有的买卖关系所能具备的。在“义气”的故纸堆里,我们看到的只是放大的“人情”,找不到“法治规则”的身影。更何况,小农的思想里,本身就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欺生”的狡黠。因为他与外界的交易,即使有,也往往是一次性的,故而“欺骗一次又何妨”。
于是我们见到了今天中国市场秩序中诚信的极度缺失。这个问题恐怕不是靠弘扬传统的“义”文化所能解决的。我想问的是,平等、诚信、负责的商业精神的种子,在中国这块缺少适宜养分的土地上,能否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抑或,就象西方文明的其他因子在中国的命运一样,等待我们的又是一场“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的结局?
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一些有良心的学者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我理解,诚信文化在全社会普遍的养成,本身就是“好的市场经济”所依赖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诚信立法”,这个过程一定会比较缓慢,所以,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容忍”。作者:赵少钦
您在这个论坛的权限: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回复主题